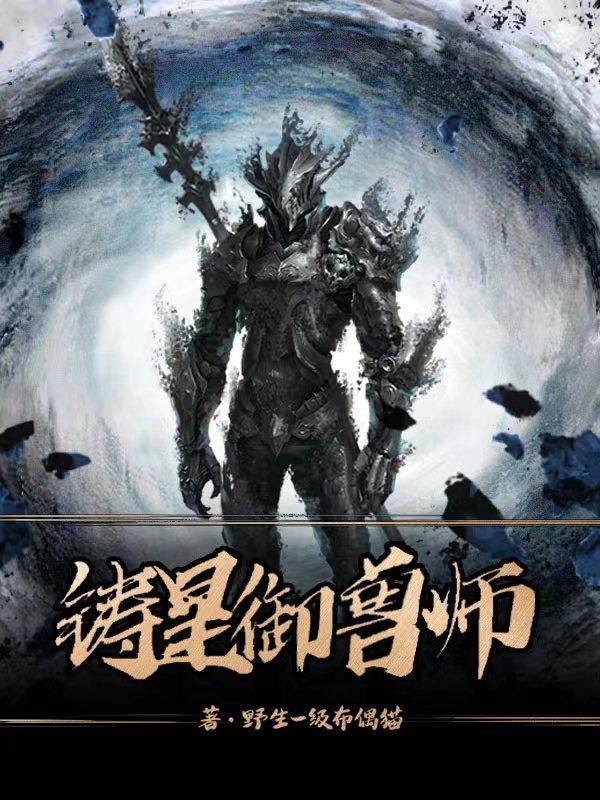恋上你看书>穿书农门粮满仓,我为权臣牵红线 > 第64章 官兵封村(第1页)
第64章 官兵封村(第1页)
章家老两口听得“鼠疫”二字,老汉的旱烟杆当啷落地,老妇踉跄着跌坐在条凳上,压得榫头吱呀作响。
“公婆千万保重!”大儿媳搀着二老,指甲掐进掌心,“二郎正当壮年”话没说完自己先哽咽了。
余巧巧扯了扯老郎中补丁摞补丁的衣袖:“虽非医者,但晚辈记得疫病须得熏药净屋,病患更要独居一室。”
“正是此理。”老郎中从褡裢摸出几包草药,“你与章娘子速去寻村长,叫全村洒扫熏艾。尤其药汤火候,定要亲眼盯着。”
暮色中惊起几只昏鸦。章村长立在祠堂前的石碾上,铜锣“咣”地一敲:“今日起各家熏药避秽!”话音未落,底下炸开了锅。
“五十二年前柳树沟那场大疫”有个佝偻老头颤巍巍举手,“我爹说染病的浑身冒血泡,三日内必死。”
“快逃吧!”裹着头巾的妇人抱紧婴孩,“趁官道还没封死。”
“往哪逃?”后生红着眼吼,“西边十几个村早死绝了!”
章村长抡起鼓槌砸向铜锣:“都给我住嘴!”震得檐下麻雀乱飞,“看见那位穿青布衫的姑娘没?人家舍命来帮咱们,你们倒要当缩头王八?”
百十双眼睛齐刷刷望来。余巧巧攥紧药包,忽听人群里冒出句:“这不是山腰老瞎子家的亲戚么?”
“对对!”豁牙少年挤到前头,“我晌午见老瞎子给人扎针呢!”
方才安静的人群又骚动起来。穿短打的汉子冷笑:“那疯子去年还说我有肺痨,如今不照样活蹦乱跳?”
“村长莫不是诓咱们?”老妇啐了口唾沫,“让个疯瞎子治病,还不如跳河痛快!”
余巧巧正要开口,忽见章娘子抱着药罐挤进人群:“都闭嘴!”
这素日温婉的妇人竟红了眼,“我家虎子高热三日,老神仙施针后已能进米汤了!”
祠堂霎时寂静。
暮风卷着艾草灰掠过众人发梢,不知谁家婴孩突然啼哭,倒衬得那哭声明亮得很。
“信与不信,各自思量。”余巧巧解开药包,焦苦气扑面而来,“这是老郎中配的祛疫散,愿领的上前登记。”
最先伸手的是个跛脚汉子:“横竖是个死,老子赌了!”他撩起衣襟兜住药粉,一瘸一拐往家跑。渐渐地,七八只手探向药包,像溺水者抓住浮木。
章村长抹了把额汗,刚要说话,村东头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。余巧巧心头一跳——那方向,正是老郎中问诊的院落。
子时的梆子声刚落,麻瓜村上空浮着层青灰色药雾。
余巧巧踩着露水回村长家时,檐下挂的艾草还在冒烟。
章娘子端着铜盆候在廊下:“当家的让人捎话,说要腾祠堂作病坊。”说着递来热帕子,“姑娘擦把脸。”
余巧巧绞干布巾,青砖地洇开一圈水渍。忽闻西墙根传来窸窣声,像是谁在搬动陶瓮。
“怕是张屠户家要跑。”章娘子攥紧木盆沿,“他家小儿今早还帮着埋鼠。”
“人之常情。”余巧巧趿着布鞋往厢房走,“若换作你我,未必不逃。”
油灯噗地灭了。
章娘子摸黑坐在炕沿,“姑娘说句实话,我们村还有救么?”